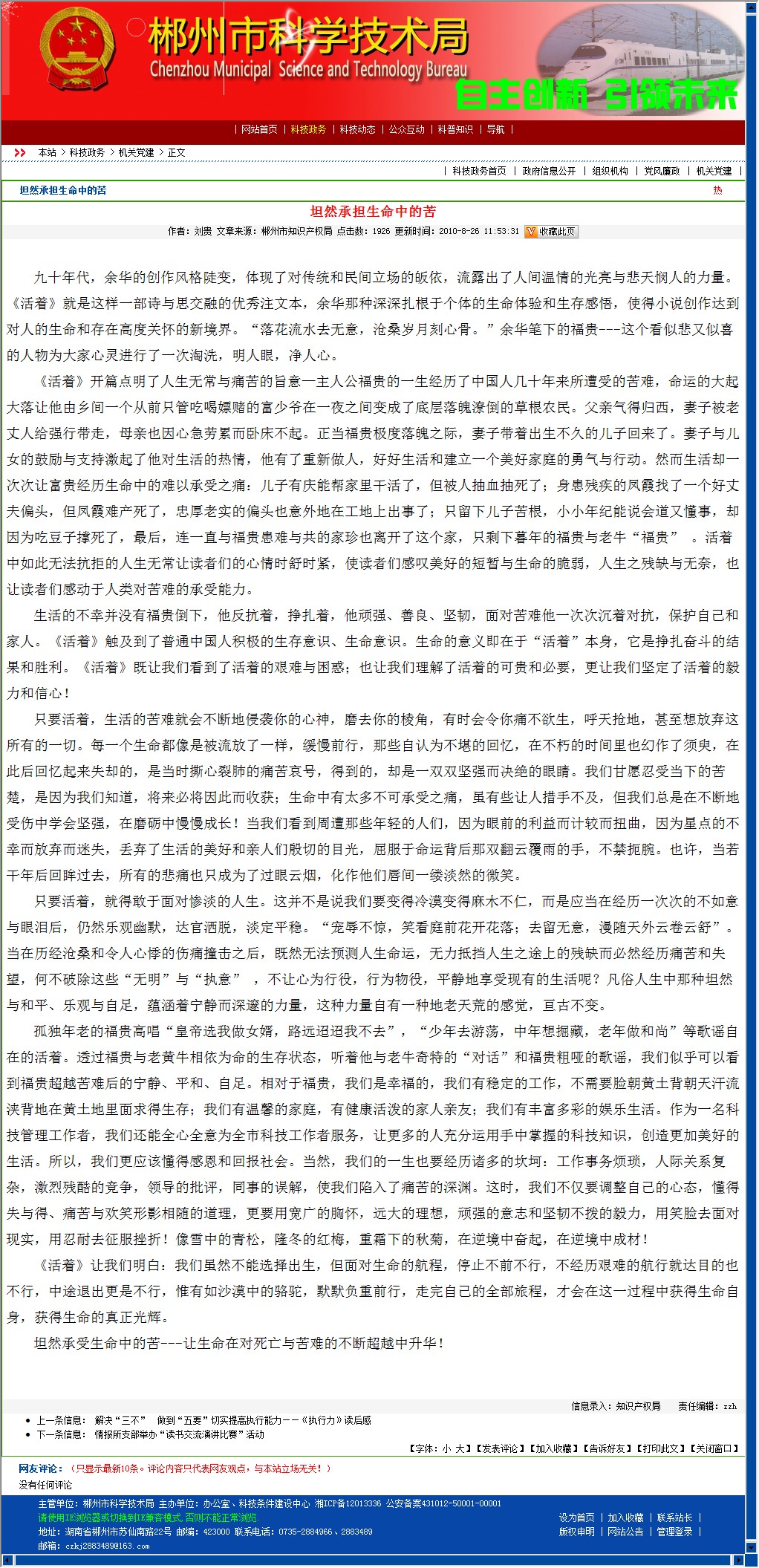九十年代,余华的创作风格陡变,体现了对传统和民间立场的皈依,流露出了人间温情的光亮与悲天悯人的力量。《活着》就是这样一部诗与思交融的优秀注文本,余华那种深深扎根于个体的生命体验和生存感悟,使得小说创作达到对人的生命和存在高度关怀的新境界。“落花流水去无意,沧桑岁月刻心骨。”余华笔下的福贵---这个看似悲又似喜的人物为大家心灵进行了一次淘洗,明人眼,净人心。
《活着》开篇点明了人生无常与痛苦的旨意—主人公福贵的一生经历了中国人几十年来所遭受的苦难,命运的大起大落让他由乡间一个从前只管吃喝嫖赌的富少爷在一夜之间变成了底层落魄潦倒的草根农民。父亲气得归西,妻子被老丈人给强行带走,母亲也因心急劳累而卧床不起。正当福贵极度落魄之际,妻子带着出生不久的儿子回来了。妻子与儿女的鼓励与支持激起了他对生活的热情,他有了重新做人,好好生活和建立一个美好家庭的勇气与行动。然而生活却一次次让富贵经历生命中的难以承受之痛:儿子有庆能帮家里干活了,但被人抽血抽死了;身患残疾的凤霞找了一个好丈夫偏头,但凤霞难产死了,忠厚老实的偏头也意外地在工地上出事了;只留下儿子苦根,小小年纪能说会道又懂事,却因为吃豆子撑死了,最后,连一直与福贵患难与共的家珍也离开了这个家,只剩下暮年的福贵与老牛“福贵” 。活着中如此无法抗拒的人生无常让读者们的心情时舒时紧,使读者们感叹美好的短暂与生命的脆弱,人生之残缺与无奈,也让读者们感动于人类对苦难的承受能力。
生活的不幸并没有福贵倒下,他反抗着,挣扎着,他顽强、善良、坚韧,面对苦难他一次次沉着对抗,保护自己和家人。《活着》触及到了普通中国人积极的生存意识、生命意识。生命的意义即在于“活着”本身,它是挣扎奋斗的结果和胜利。《活着》既让我们看到了活着的艰难与困惑;也让我们理解了活着的可贵和必要,更让我们坚定了活着的毅力和信心!
只要活着,生活的苦难就会不断地侵袭你的心神,磨去你的棱角,有时会令你痛不欲生,呼天抢地,甚至想放弃这所有的一切。每一个生命都像是被流放了一样,缓慢前行,那些自认为不堪的回忆,在不朽的时间里也幻作了须臾,在此后回忆起来失却的,是当时撕心裂肺的痛苦哀号,得到的,却是一双双坚强而决绝的眼睛。我们甘愿忍受当下的苦楚,是因为我们知道,将来必将因此而收获;生命中有太多不可承受之痛,虽有些让人措手不及,但我们总是在不断地受伤中学会坚强,在磨砺中慢慢成长!当我们看到周遭那些年轻的人们,因为眼前的利益而计较而扭曲,因为星点的不幸而放弃而迷失,丢弃了生活的美好和亲人们殷切的目光,屈服于命运背后那双翻云覆雨的手,不禁扼腕。也许,当若干年后回眸过去,所有的悲痛也只成为了过眼云烟,化作他们唇间一缕淡然的微笑。
只要活着,就得敢于面对惨淡的人生。这并不是说我们要变得冷漠变得麻木不仁,而是应当在经历一次次的不如意与眼泪后,仍然乐观幽默,达官洒脱,淡定平稳。“宠辱不惊,笑看庭前花开花落;去留无意,漫随天外云卷云舒”。当在历经沧桑和令人心悸的伤痛撞击之后,既然无法预测人生命运,无力抵挡人生之途上的残缺而必然经历痛苦和失望,何不破除这些“无明”与“执意” ,不让心为行役,行为物役,平静地享受现有的生活呢?凡俗人生中那种坦然与和平、乐观与自足,蕴涵着宁静而深邃的力量,这种力量自有一种地老天荒的感觉,亘古不变。
孤独年老的福贵高唱“皇帝选我做女婿,路远迢迢我不去”,“少年去游荡,中年想掘藏,老年做和尚”等歌谣自在的活着。透过福贵与老黄牛相依为命的生存状态,听着他与老牛奇特的“对话”和福贵粗哑的歌谣,我们似乎可以看到福贵超越苦难后的宁静、平和、自足。相对于福贵,我们是幸福的,我们有稳定的工作,不需要脸朝黄土背朝天汗流浃背地在黄土地里面求得生存;我们有温馨的家庭,有健康活泼的家人亲友;我们有丰富多彩的娱乐生活。作为一名科技管理工作者,我们还能全心全意为全市科技工作者服务,让更多的人充分运用手中掌握的科技知识,创造更加美好的生活。所以,我们更应该懂得感恩和回报社会。当然,我们的一生也要经历诸多的坎坷:工作事务烦琐,人际关系复杂,激烈残酷的竞争,领导的批评,同事的误解,使我们陷入了痛苦的深渊。这时,我们不仅要调整自己的心态,懂得失与得、痛苦与欢笑形影相随的道理,更要用宽广的胸怀,远大的理想,顽强的意志和坚韧不拨的毅力,用笑脸去面对现实,用忍耐去征服挫折!像雪中的青松,隆冬的红梅,重霜下的秋菊,在逆境中奋起,在逆境中成材!
《活着》让我们明白:我们虽然不能选择出生,但面对生命的航程,停止不前不行,不经历艰难的航行就达目的也不行,中途退出更是不行,惟有如沙漠中的骆驼,默默负重前行,走完自己的全部旅程,才会在这一过程中获得生命自身,获得生命的真正光辉。
坦然承受生命中的苦---让生命在对死亡与苦难的不断超越中升华!